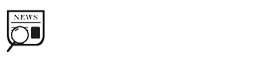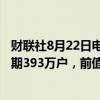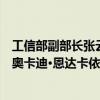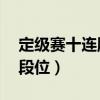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实习记者 刘溢衎 作为北京的一名老村医,杨弘文坚守在基层卫生一线已有三十个年头。近几年,他扮演的角色正不断被削弱,对于未来他也感到很迷茫。
杨弘文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从业初期,村里二十多位病人足以让自己从早忙到晚。但现在由于患者减少,看病已不再是他的主业。更多时间,他都是在给患者拿药、进行慢性病管理、入户调查、新生儿登记等。
杨弘文所在的村子约有1500人。他说:“来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少,一天也遇不到几位病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1.6万个,比上一年增加了3.6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3.4万个,与去年持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万个,门诊部(所)32.1万个,均为正增长;村卫生室58.8万个,比去年减少了5000个。
在社区和门诊等基层医疗机构数量增长的同时,村级卫生室的数量却出现了下降。这背后隐藏的是患者数量减少、药物供应不足、乡村医生待遇较低等问题。杨弘文的经历,正是中国许多村卫生室现状的缩影。
北京大学国发院博雅特聘教授、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基层卫生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不仅是村医本身的待遇和培训问题,更多还牵扯到村医的定位问题,应该将他们定位为“赤脚医生”,还是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医生,这些疑问需要因地制宜地去解决。
村医工资少,卫生室设备匮乏
杨弘文和其他村医每年都会接受一到两次由区里医生提供的统一培训,包括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培训的内容涉及常见病处理、传染病防控以及中医适宜技术等。他观察到,尽管培训内容丰富,但目前主要以线上学习为主,实操环节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不多,且实操机会也在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医的专业发展和技能提升。
此外,药品短缺问题也导致患者数量减少。根据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杨弘文所在卫生室的药物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调配和补充。由于药品的保质期通常为3年至5年,对于治疗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的药物,进货量更少,通常只有三五盒。随着药品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卫生室的服务能力也在逐步下降。
杨弘文表示,他所在的乡镇共有28个村,其中还有5个村的卫生室未实行医保报销政策,因此村民基本不会来这里挂号买药。随着医保政策的普及,人们更倾向去可以报销的大医院就诊和拿药。“谁还会选择自费看病取药的卫生室呢?”他说。
据杨弘文所在村的一位村民反映,过去卫生室提供输液和注射服务,但后来这些医疗服务被禁止,村民不得不前往镇上或区级医院就诊。一般情况下,感冒和轻微外伤等小病会在村卫生室就近处理,其他疾病则需要到大医院治疗。另一位村民称,由于腿脚不便,很少有机会去大医院,只有在卫生室无法治疗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大医院。目前,卫生室主要满足村民看小病和开具普通药物的需求。
刘国恩认为,边远农村地区的医疗取决于有多少村民仍然愿意来卫生室看病就医,以及村民生活环境是否有变化。如果村落环境没有变化,村民自然就不会减弱对村卫生室的需求。但就现状而言,村民不愿意来的最主要原因是卫生室药物少、医资薄弱,不能满足村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从而不得不向大医院求助。
除了药品缺乏、服务能力下降外,村卫生室的办公条件简陋和软件设施不足也制约了其发展。许多卫生室空间有限,外观简陋,往往是由村医在附近搭建的房屋里进行医疗服务。杨弘文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原本应由村委会配备的一套三居室的小诊所未能供他使用,而村委会和区里既未给出明确答复,也没有为他建造新的卫生室,导致他不得不在家附近腾出一间房作为临时卫生室。
在北京郊区另一个村子的村医梁瑾瑜,“掌管”着约600人的健康,她所在的卫生室是由自家车库改造的,面积狭小,仅一间房。梁瑾瑜说,尽管村里曾计划拨款建房,但至今未见实施。
这种情况在乡村并不鲜见。大多数诊所仅设有一间诊室,用于开药和看病,只有少数卫生室配备了药房、诊室、治疗室等多功能房间。杨弘文和梁瑾瑜都表示,他们所在的卫生室在建设补助方面存在不足,简陋的环境很难满足患者的就医习惯和对医疗环境的要求。
实际上,早在201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就提出,村卫生室房屋建设规模不低于60平方米,服务人口多的应当适当调增建筑面积。村卫生室至少设有诊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和药房。经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准,开展静脉给药服务项目的增设观察室,根据需要设立值班室,鼓励有条件的设立康复室。
但在杨、梁两位大夫的卫生室中,诊室、治疗室和药房都挤在一个房间内。
在梁瑾瑜卫生室的工作台上,摆放着一本厚重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工作手册》,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位病人的健康信息。由于她没有自费购买电脑,因此所有相关的患者信息和药物采购信息都由她手写完成。
资金不足也导致一些乡村医生对患者和药物信息无法进行信息化管理。梁瑾瑜说,那些配备了软件设备的卫生室通常会将患者信息输入到电脑中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电脑的卫生室,则会用手写的方式记录患者信息。不论是电子录入还是手写记录,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在每年年底整理成纸质版上报。
年轻人不愿来
杨弘文所在的村庄,村医的月薪为5500元,由地方财政部门统一支付,所有村医都有社保。根据国家规定,持有三证(乡村医生证、乡村医生职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乡村医生,男性年满60岁、女性年满55岁,并且在村级连续执业35年以上(含35年),每人每月可获得1080元的退休金。
杨弘文说,之前已退休的老大夫,算上每月1000元的补助,现在月退休金能达到两千多元。
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同行业中相比并不具备竞争力。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24年6月发布的《全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及工资情况(2023年)》报告,卫生和社会工作的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约为24.2万元。相比之下,村医的年收入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27%。
在杨弘文看来,村医本质上还是过去的“赤脚医生”,身份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享受的政策待遇与村里的普通农民相同。他回忆20年前的情况,并坦言保险政策的变动让他从最初的乐观变得迷茫。
他说:“直到2016年左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才开始为我们缴纳最低标准的城镇职工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我退休时,缴纳年限也才10年左右,医保的缴纳情况就差得更多了。即便我们想要补交,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没有明确的补交规定和方式。乡村医生的待遇缺乏保障,留不住人也情有可原。”
目前,北京的大多数村医是根据“区聘村管民用”政策来聘用的,即区政府负责招聘乡村医生,村委会代为管理村医和卫生室,以服务当地村民。招聘通常遵循就近原则,有意愿的医生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配,只有少数乡村医生是通过自己考取医师资格证书来应聘的。
杨弘文的情况属于前者,没有考取专业的(医生)资格证。而梁瑾瑜是在卫校,专门为了应聘村医考取了资格证。她说:“附近的村子,只有我有医生资格证。”
梁瑾瑜观察到,每年都会有十多位大学生来村卫生室实习,但最终没有人选择留下。去年她曾指导过两位大学生,他们明确表示,来实习主要是为了获得必要的实训学分,内心并不愿意留在村里成为村医。目前,这两位大学生已经选择去区医院实习。
梁瑾瑜说,尽管许多医学院校的学生与学校签订了合同,参与了村医定向培养专业,但从前年的情况来看,大约有一百余人报名,但在实习和毕业后,约70%的学生都选择了违约,不愿意到基层担任村医。杨弘文也认为,村医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难。
刘国恩认为,村医萎缩的情况一直存在,但农村边远地区的医疗服务会逐渐向城市化转移,同时医疗服务的人才也有向城市发展的趋势。农村会逐渐融入城市,村医的概念也会随之转变,医疗服务体系也应该转型升级。高校毕业生短期去偏远地区培训学习是可以被接受的,长期来看不现实。
除了上述问题,仅通过“区聘”方式很难批量招来医生,许多在基层卫生室实习的大学生毕业后并不会选择留在基层工作。杨弘文提到,他所接受的培训在实际诊疗中难以得到应用,而且与大医院相比,村医缺乏更多的晋升机会,这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空间。当毕业生或实习生看到老村医的现状和退休情况后,往往会放弃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想法。
政策有待落实
2023年4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的通知》,指出要深化城市医院支援县级医院工作、部署县级以上医院支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开展县乡村巡回医疗等,政策的出台需要各级医疗部门落到实处。
尽管政策有所改变,但村医和卫生室的实际情况并未得到太多改善。杨弘文说:“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家发布了诸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文件,但这些政策在我们这些偏远乡村未得到有效落实,包括人才培养和完善乡村医疗人才队伍等措施。”但他认为,分级诊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只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病患对村卫生室的不信任,不愿意自费就诊等问题。
刘国恩表示,国家不断出台的分级诊疗制度也是为了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过去十多年数据显示,大医院的虹吸效应使得普通的病人也要在大医院中看诊,削弱了基层医疗的能力,且基层医疗卫生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林敏在发表的《加快乡村医疗互助发展》一文中提出,目前乡村医疗互助保障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相应的政策和工作体系;在各地推进的乡村医疗互助帮扶保障体系实践中,省域间推广的成效差异显著,亟须研究解决。
林敏建议,在国家层面,尽快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将“加快乡村医疗互助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纳入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明确乡村医疗互助的定位和工作目标。由国家乡村振兴局提炼总结乡村医疗互助经验,制定加快乡村医疗互助发展的工作方案,统筹管理并全面推广乡村医疗互助。
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通知》,指出争取在2024年年底实现村卫生室看病刷医保。这也是杨弘文所期望的事。
刘国恩认为,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村医培训并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从长远来看,农村应顺应发展趋势,逐步融入城市化进程,这是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的必然选择。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面考虑如何缩短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医疗服务之间的鸿沟,并改善医疗卫生政策。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人力资源的发展,即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医务人员的作用。”刘国恩指出:“目前,质量好的医务人员多数都在大医院,不是总量(每千人的医生数)有问题,而是医务人员的机制出现了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导致很多医生被‘绑’在大医院。为此,需要对体制作出改变,要鼓励医务人员走出大医院。”
刘国恩说,如果更多的医务人员从大医院中“解放”出来,解除桎梏,走向社会和社区,将有助于建立更多的社会诊所。这样一来,常见性疾病将得到更有效地治疗,同时也能减轻大医院的医疗服务压力,从而为重症和急诊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更多的方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弘文、梁瑾瑜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