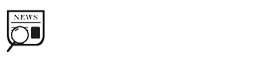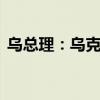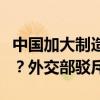王入秋/文
在人生的低谷,享受“休息的权利”
1990年代初始,日本就从经济飞速发展、一切蒸蒸日上的希望年代,快速转向泡沫经济崩溃的社会状态,股市腰斩、房地产暴雷、企业大规模破产,日本人后知后觉地把平成时代(1989年至2019年),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1996年4月,一档叫《悠长假期》的新剧开播,在主角居住的3层老旧小楼楼顶,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坐在沙滩上一男一女望向大海,下面醒目地写着一行英文:“DON’TWORRY,BEHAPPY(别烦恼,要开心)”。
或许是因为主演山口智子和木村拓哉的号召力,或许是因为这部剧的立意切中了时代浪潮中人们积郁的心结,很快《悠长假期》就掀起了风潮,大结局收视率高达36.7%,成为近30年日剧史上收视率第六高的剧作。
所谓“悠长假期”,并非是儿时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寒暑假,而是那些被卡住的“人生的低谷”。人活着,难免会遇到低谷,或许因为个人成长遇到瓶颈,或许因为身处经济衰退,只能在破碎的泡沫中抱住浮木,随社会浪潮上下颠簸。
《悠长假期》中的男女主就是处于各自人生低谷的人。女主小南是一个在30岁的尾声被未婚夫逃婚的过气模特,她去未婚夫租住的公寓找人,却发现对方早已离去。公寓里只剩下从艺术学院钢琴系毕业、考研究生失败、在儿童音乐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濑名。小南在走投无路时半哀求、半耍无赖地成了濑名的舍友,带着她几十瓶被退回的婚礼用红酒住进了濑名的公寓——那装红酒的木箱成了客厅的茶几,而那些看似永远喝不完的红酒到“长假”结束,正好喝完。
剧中第二集,编剧北川悦吏子就借不得志的24岁钢琴家濑名之口,点明了这部剧的题眼:“人总有不顺利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在那种时候,我就把它当作神赐的假期,不必勉强冲刺,不必紧张,不必加油,一切顺其自然。”在听了这番安慰的话后,小南问道:“然后呢?”濑名说:“就会好转。”“真的吗?”“大概会的。”
这里的比喻巧妙地让人在“被动的低谷”,获得了“过假期的主动权”,同时,成年人的目标与价值不再只有向上攀爬、获得成功、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也有了“过假期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将现实浪漫化而已,而是一种健康且有智慧的思考方式。
但对于刚刚经历过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人们来说,接受这样的思考方式并没有那么容易。在社会蓬勃发展的阶段,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努力工作、投资、买房,就“能够”获得更多回报,那些回报也足够可观,所以人们愿意投入更多时间、提高效率,来换取更多的报酬。在这样的惯性下,人一旦停下来,就会觉得“错过了些什么”,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就会爆发。在《倦怠社会》中,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剖析了这样一种“过度积极”的状态和它所引起的抑郁:“当功绩主体不再能够(继续工作)时,抑郁症就在这一时刻爆发……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抑郁症患者是这场内在战争中的伤残者。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它所反映的,是那种同自身作战的人类。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
《倦怠社会》
[德] 韩炳哲 | 著
王一力| 译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在这样的强迫性积极中,“休息”成了一种缺失的能力。停下来的人会不知道做什么,被焦虑侵袭大脑,害怕无法走出低谷期,甚至会想:“我有什么资格度假?”但是,人并不是一定要获得什么成就,才能休息的。在《赞美闲散》一书中,英国哲学家罗素点明了休息对于个体人生的重要价值:“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
《赞美闲散》
[英]伯特兰·罗素 | 著
仝欣| 译
浦睿文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5月
同时,这也指出了人生的“悠长假期”所包含的建设性价值。当处于工作中时,人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运作,他的目标、行动,都以工作系统的价值和导向为主体来运作,他的“主动性”自然大部分消耗在工作中,而非自己的整体人生上。越是身处于资源集中的都市,人越会处于“被动”的状态中:“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赞美闲散》)所以这种低谷期被动的“停下来”,其实是自己重新审视自己拥有的土地、种上新的种子的机会,它或许关系到你未来10年、20年的人生方向。
在《悠长假期》中,事业、爱情均遭受打击的小南接受了濑名的这一比喻,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善意与支持。而这种低谷期仍保持的善良底色,也正与濑名的人生态度相关。正是他的松弛与不强求带来的安全感,滋养了他的善良天性。因为不论我们多么努力,多么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艰苦劳碌也无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余裕,没有余裕,也就难以看见、去爱、去支持与自己不一样的“他者”。
爱情的发生,并不允诺“安全”
作为28年前的古早日剧,《悠长假期》可以说是开创了“先一起生活,最后再相爱”的都市剧模式的鼻祖。温吞的、会在关键时刻退缩的濑名和“会万古长青”(逃婚的未婚夫的评价)的小南在故事中都有比彼此更接近于“爱情”的对象,直到剧情的尾声,才意识到对彼此的感情。
剧中的年轻人们,也都在约会中不断实践,来探索“对方到底是不是合适的人”,这在现在看来,当然会有些政治不正确。在剧情的初期,濑名暗恋自己文静、内向却很坚韧的学妹凉子(由松隆子饰演),而从未谈过恋爱的凉子却懵懂地喜欢上了野兽般的恋爱进攻型选手真二(由竹野内丰饰演),此时真二有一位女朋友留美(由凉饰演)。凉子在意识到自己对真二的心意后,立刻拒绝了追求自己的濑名,并沉浸在“为什么会爱上不该爱的人”的痛苦感受之中。女主小南的闺蜜桃子(在本剧中,桃子类似于一个“爱神”的角色)去探望凉子,对她说:“人生只有一次,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感受)呢?”
于是,桃子拉着凉子去向真二告白,凉子面对众人无法开口,小南责备桃子制造混乱,让喜欢凉子的濑名、真二的女友留美受伤。凉子无法面对这样的场面,跑了出去。濑名拉起真二追了出去,让真二听听凉子到底想说什么。就这样,凉子和真二开始了恋爱。
在这段修罗场般的情节中,众人有两个一以贯之的行事准则——一是,“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二是,爱的选择出自感受,而不是条件的选择和对人的价值的排序。这两个众人共识般的核心准则,就是1996年人们对爱与亲密关系的认知与当下大部分人对爱情的认知的差异所在。
在《悠长假期》中,年轻人们似乎都有着令当下观众羡慕的“稳定内核”,他们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尊重他人的感受,不计算,在意识到自己心意的时候,就坦率地表达。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论男女,在爱情中被选择时,都不会彻底沦为被挑选、评判的“客体”,因此也不会被动地陷入“雄竞”“雌竞”的思维。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对于感情的波澜都有共识:“对方没有更爱我,不是因为我不够好,而是出于对方的感受。”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样的思维下,身处修罗场中就不会受到伤害,不会痛,只是这种痛感,并不会因为把自己的价值由对方的选择来定义,而导向强烈的自我攻击。
这种在爱情中强烈的“自我攻击”其实是过度“自恋”的结果,因为看不见他人也有选择的权利、把他人当成“自我的倒影”,而将一切原因归咎于自己。在《爱欲之死》中,韩炳哲就剖析了当下人们如何因为自恋,而削弱了爱的能力:“自恋与自爱不同。自爱的主体以自我为出发点,与他者明确划清界限;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
《爱欲之死》
[德] 韩炳哲 | 著
宋娀 | 译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而自恋的主体,最核心的追求就是“成功”,表现在爱情中的“成功”就是,快速征服对方,让对方作出承诺,坚守恋爱、婚姻关系里的道德,从而为自己提供“安全感”。但是,安全感真的是爱的主要需求吗?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指出:“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的感受罢了。”
把安全感置于首要需求的位置,正映射出主体自身的脆弱与焦虑,而往往,这种脆弱与焦虑是人们不自知,或者说不愿承认的。正是这种不安全感,驱动当下的人们去争取爱情的成功,来获得保障,但是在爱的探索阶段的所有不确定性,都化作了自我攻击的素材,让隐藏的脆弱和焦虑在体内熊熊燃烧。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恪守恋爱“应当”如何进展的安全准则,爱的感受被削弱,人们互相成为对方“被投以爱的期待的对象”,很难有真正的互动。于是,在少有感受,却有大把情绪的情况下,爱情本身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它本身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爱被当成一种享受的形式被积极化了。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愉悦感受,不应有情节、有故事或者带有戏剧性而应该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感情和刺激。它必须免于受到伤害、攻击、打击等负面行为的影响。爱的消退本身已经是相当消极的事情了。但这些消极面其实是爱的本质的一部分:‘爱不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基于我们的努力和积极态度而存在,它可以没来由地打击我们,伤害我们。’”(《爱欲之死》)
在《悠长假期》中,男女主角濑名和小南一起度过低谷,接纳对方的“无能为力”,一同玩耍,互相洞察和支持对方的“想要”。这一切的实践并非以“潜在恋爱对象”的身份出发,也不是为了获得承诺和安全感,而是出自两个性格迥异、价值观相似的普通人的立场。这反而实现了健康的爱情里的“共同建构”。
仅仅凭借相遇,就想立刻拥有绝对的安全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因为正如巴迪欧所说:“爱不能被简化为相遇,因为爱首先是一种建构。”
爱是一系列“建构”
在确认恋人对自己的爱意时,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和某某人同时掉到水里,你只能救一个人,你选择救谁?”这个问题很严肃又很荒诞,虚拟出来的绝境令人生畏,爱情似乎无端变成了生死攸关的责任。
在《悠长假期》里,小南的闺蜜桃子将这个问题进行了转换,提出了一个巧妙的问题:“去便利店买啤酒的时候,顺便买了烟花,在夏夜晚风中,你会想和谁一起放烟花呢?”正是这个极具感受性的、关于普通日常中的“庆典”的问题,点醒了小南,让她意识到了自己对濑名的感情。
在濑名和小南的相处中,“玩耍”是他们的互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他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小南在客厅喝着本来打算在婚礼时开的昂贵红酒(这瓶红酒的年份正是她出生的年份),拿着未婚夫留下的一个弹力球,给濑名讲述未婚夫曾经在凌晨为自己庆祝生日的过往。在这有些忧伤的氛围中,濑名拿过弹力球,把小南叫到窗边,和她说,从3楼把球扔下去,可以弹回来稳稳接在手里,小南说她才不信。而弹力球居然真的落地、弹起,被濑名接住了。小南一下子开心起来,也扔了一次,在她接住弹力球的时候,之前的失落烟消云散。
作为成年人生活在总要有“目标”的社会中,我们似乎低估了像孩子一样“玩耍”的价值。需要消遣的时候,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和朋友去吃顿大餐,或者对着屏幕玩游戏,刷剧,甚至干脆刷起短视频,沉浸在大数据提供的刺激之中。但这些好像又很难真的给我们带来高质量的满足感。究其原因或许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玩耍”仍旧是一种以消费为主要目标的行为——“在如今的超资本主义中,人的存在彻底瓦解,融入了商品关系编织的网络。没有一个生活领域能够摆脱商业的控制。超级资本主义把一切人类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它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市场价值。”(《倦怠社会》)
不论是夏夜放烟火、扔下弹力球再接住,还是濑名和小南在楼下投篮球、玩些类似“成语接龙”的语言游戏、走路把自己的步伐调整成和对方的左右脚一致,这些看似无聊的玩闹,其实将人从“目标”和思虑中拉了出来,创造了快乐。
在《倦怠社会》一书中,韩炳哲强调了“庆祝”和玩耍对于当下的人的重要性:“‘庆祝’一词取消了一切目的,人们无须为了抵达某处而刻意前往。由于节日的存在,时间不再是一连串飘忽即逝、仓促的时刻……庆祝和消逝是相反的。在节日庆典中,一切都不会消散而去。在这一意义上,庆典时刻是永恒的。”
这种玩耍与庆祝的状态,脱离了效率和目标,让人的时间不再是一种被抢夺的资源,而是与自己的感受相连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新型叙事,由此产生一个新时代、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中解救出来”。(《倦怠社会》)在这样孩童般的庆祝和玩耍中,我们同伙伴一起感到快乐,惊叹于小小的“奇迹”,并从中获得安慰。
在濑名与小南的关系中,除了玩耍,还有另一重至关重要的建构,就是对彼此的“想要”的洞察与支持。作为钢琴家的濑名是一个温柔,但有些优柔寡断的人,他的导师曾对他说:“濑名,你是一个不会把‘寂寞’说出口的人,听你的琴声就能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说自己寂寞,你也不会说。你是很强的人,正因为很强大,所以温柔。”濑名回应道:“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很软弱。”“软弱也不错,软弱也是一种纯真。能让自己更坦率就好了,热就开窗,冷就开暖炉。当然,不需要在大家面前这样,只要在某个人面前,请把你的墙壁冲破吧。”导师之所以会说这番话,是因为这种无法把想说的话坦率说出口的状态正是濑名钢琴演奏瓶颈的症结,濑名弹钢琴像是在与之搏斗,而不像是在诉说和表达。
小南是能够洞察到濑名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的人,她感受到了濑名对她的支持和包容,也明白濑名那些并非用语言表达的心意。更重要的是,小南是个无比坦率的人,她在搬离濑名的公寓前,与濑名大吵了一架,第二天早上本想不辞而别,但她走到楼下,大喊濑名,对他说:“虽然昨天想要把你大卸八块,但今天要走了还是会感到寂寞。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然后转身大步离开。这种不留遗憾的坦率,何尝不是对关系的建构呢?
而在关系中更强有力的支持,是让对方“成为他自己”。在濑名要放弃钢琴的时候,面对别人说的“没有天赋的人背后没有翅膀”的评价,小南脱口而出:“濑名有世界上最大的翅膀。”然后,小南学会了濑名为她演奏的曲子,并告诉濑名:“你的琴声在我被抛弃的时候拯救了我。你说没有奇迹,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一个星期学会就是奇迹。你不能放弃钢琴。”彼时的小南并没有和濑名成为恋人,她只是无法抑制地想要守护住对方最重要的东西。
这让人想起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的结语:“爱,就是用世界上既有的一切来赋予生命以活力,打破和跨越孤独。在这个世界中,我很直接地感受到,幸福的源泉就在于与他人共在。‘我爱你’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你成为我生命的源泉。在这个源泉的泉水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欢乐,首先是你的欢乐。”
《爱的多重奏》
[法] 阿兰·巴迪欧 | 著
邓刚| 译
六点图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